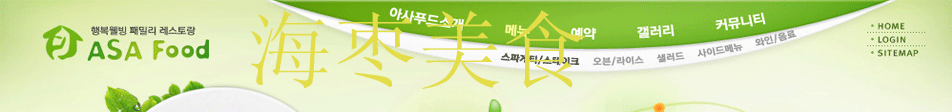|
治疗白癜风的有效方法 http://www.baidianfeng51.cn/baidianfengzixun/wuliliaofa/294.html 作者:张宇铭,本文为作者年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摘要 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的大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时期的蒙古汗国内部长期分裂、各部族间战争频繁,外部女真族正值兴起、四面扩张。在其执政的30年期间,为了能与汉民族和女真族两方政权抗衡,完成蒙古民族的重新强大和统一,其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修建了自己的统治中心一一察罕浩特。由于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宗教因素以及个人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最终以败亡告终,但他对17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进程及蒙古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察罕浩特遗址是目前赤峰市境内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城市遗址,虽然历经四百余年,但至今为止城墙和宫殿基址尚未遭到严重破坏。其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为丘陵草原地貌,草原河流纵横、土壤肥沃;北接大兴安岭山脉南麓,高耸的山脉阻挡了北方寒流的南下,使得气候冬暖夏凉,其环境适合人类在此生产生活;东侧一道自然形成的山谷横穿大兴安岭,形成了蒙古高原通往松辽平原的天然通道,因此具有十分优越的交通地位和战略地位。林丹汗将在此处建设都城于这些方面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林丹汗在与后金争斗的后期处于劣势,而选择了率领察哈尔本部西迁,在他身亡青海后,其子向后金投降,察罕浩特作为林丹汗的政治中心遂告结束,察罕浩特逐渐被废弃,后来随着当地人口的陆续南迁,原来的都城逐渐沦为废墟。 本文在史料和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林丹汗及察罕浩特进行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介绍察哈尔蒙古变迁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及来到漠南后的历史; 二、林丹汗时期的察哈尔对外与明朝及后金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对内与其他蒙古部族关系的转变,所决定的当时修建察罕浩特都城的必要性; 三、林丹汗后期的察哈尔部西迁及林丹汗败亡后察罕浩特都城的废弃: 四、察罕浩特遗址的发掘情况。 绪论 (一)选题依据 蒙古族是一个伟大的游牧民族,在她辉煌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仅从蒙古族古代遗留下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城郭遗址方面来讲,在我国北方就有元大都遗址、元上都遗址、元中都遗址、鲁王城遗址、察罕浩特遗址等。上述遗址在元代和北元时期曾经是蒙古统治者繁华的都城,也是当时蒙古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察罕浩特遗址是蒙古北元游牧王朝最后的都城。与其它元上都遗址等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文化遗址相比,蒙古末代可汗察哈尔林丹汗都城察罕浩特遗址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仍处于起步阶段。 察哈尔蒙古起源于大蒙古国时期,是成吉思汗时对幼子拖雷及其夫人的封赏。在诸多蒙古部族中,他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成吉思汗从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自由人的后代中挑选的品行端正、武艺娴熟的一万人组成大汗护卫亲军——怯薛军。怯薛军是当时蒙古军团中的常备军,也是蒙古汗廷中央各类职能机构的主要成员。他们在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发起的征战中发挥了极强的战斗力。怯薛军曾是成吉思汗大军的中流砥柱,它的英雄主义精神成为蒙古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英雄主义精神在后来继承其职责的察哈尔本部护卫军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元朝灭亡后北元政权移回蒙古草原,经过明初长达20年的明蒙拉锯战中,蒙古可汗逐渐失利,将北元初期的一百万蒙古军队消耗殆尽。从而导致北元初期蒙古社会动荡,皇权旁落,蒙古统一体四分五裂,直到北元中期,蒙古社会才得以又重新组合。在此过程中,以北元汗廷后妃私人所支配的“好陈察哈尔”(意为“旧的察哈尔”)为基础,由拖雷家族其它传统“领户”组成的庞大的察哈尔群体才逐渐形成。他们以“察哈尔”的名称被命名,统称为“察哈尔万户”,并且以北元可汗直属万户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至此,察哈尔完全替代了昔日怯薛军的职责,而昔日的怯薛军则逐渐演变成独立的蒙古克什克腾部落。 十五世纪以后,察哈尔蒙古的历史对蒙古族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北元中后期和清初蒙古历史变革过程中,他们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北元后期,察哈尔万户及其政治中心察罕浩特作为蒙古游牧政权的核心,与蒙古诸部落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与明朝和后金发生频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焦点。在当时的统一全国的斗争旋涡中,以察哈尔为代表的北元蒙古游牧政权与明朝、后金政权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三大政治势力。察哈尔对明朝军事上的威胁和经济上的消耗,对后金的消极对抗以及对蒙古内部采取的强硬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加速了全国统一的进程。明朝时期,出现了北方蒙古与明政权对立的局面,17世纪上半叶随着后金的建立又出现了三足鼎立现象。察哈尔万户作为北元游牧政权的政治核心、大元可汗正统后裔直接率领的蒙古最强大的部落群体,与明朝和后来的清朝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关系,影响着当时中国历史的走向。因此,对明末清初时期的察哈尔林丹汗及其政治核心一察罕浩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林丹汗(公元年-公元年),于公元年继任蒙古大汗,统领察哈尔万户等蒙古诸万户直至公元年病死于青海大草滩,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继任汗位时年仅13岁,在其后的30年有生岁月中,一直在为完成蒙古统一,恢复元时先祖统治盛况做着不懈的努力和斗争。林丹汗统治时期正值明朝衰落和后金崛起之时,虽然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采取兴建察罕浩特都城等一系列措施,但仍难以摆脱败亡的命运。 林丹汗时期的察罕浩特都城目前城墙和宫殿的基址保存完好,尚未遭到严重破坏,从上世纪30年代到现今,国内外的学者也多次对遗址进行了考察,目前都城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已立项将察罕浩特遗址的保护与发掘工作列为年内蒙古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项目)。随着发掘的进行,大量的遗迹遗物被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林丹汗时期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实物依据。本文在研读和整理相关史料的同时,并在前人研究和发掘成果之上,试图对林丹汗和他所修建的察哈尔都城察罕浩特进行较为系统的探析。 (二)基本史料 汉文史料部分: 《明实录》是对明朝时期蒙古历史进行研究最基本的官修史料。《明实录》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作为当时明王朝主要对手的北元政权,对其资料的收集整理更是倍加重视。《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是从《明实录》中将与蒙古历史有关的资料检索出来,编成1卷本的《蒙古篇项目总索引》和10卷本的《蒙古篇》,这为研究明代蒙古历史提供了便捷。 女真及后来的清朝方面对林丹汗的相关资料,主要集中在《清实录》、《满文老档》中,而《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又为便利的研究和利用《清实录》提供了条件。当然这些史料是林丹汗曾经的对手所记载,难免有低毁、删改的内容,但对当时重大事件的记录还是较为准确的。 《明史》和《清史稿》是两部研究明、清两朝蒙古历史的重要正史。其中如《明史·鞑靼传》、《清史稿·地理志卷二十八》等资料,对研究林丹汗和察哈尔历史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明朝和北元政权的多年对峙中,明朝坚持着北边为上,东北边次之的对敌政策。从明洪武初年至明崇祯末年,为了防御北部蒙古的入侵,明朝的文官武将大量献计献策,同时也就留下了诸多记载蒙古历史的翔实资料,以及相当多的私人笔记等文字资料。《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是由薄音湖、王雄老师编辑点校,其中所收录的59种史料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察哈尔历史有关,对研究察哈尔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蒙古文史料部分: 蒙古文史料是研究林丹汗时期蒙古历史研究的另一个史料来源。《黄金史》、《金轮千福》、《蒙古源流》、《黄金史纲》、《水晶鉴》等。但这些史书都是在后金降伏蒙古后,由蒙古喇嘛或黄教信徒所撰写,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而且对林丹汗的记录都十分简略。但作为本民族所撰写的蒙古族史书,对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记录应该比较确切,所以也是研究林丹汗历史的宝贵资料。 满洲文史料部分: 《旧满洲档》、《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满文原档》等诸多满洲文史料是当时人记载林丹汗与爱新国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的第一手史料。目前因大部分满洲文档案都有了汉译版本,对满洲文档案的利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林丹汗及察哈尔万户的历史在明、蒙、金三方的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在传统的汉文史料中,基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其史料内容掺杂了较为浓厚的政治倾向;而蒙、满文字史料的记载与汉文史料记载相比则过于简单。通过对三方资料的对比和加以相互间的印证补充,希望能得到正确的史料结论,从而在研究中不会失之偏颇。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原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对于林丹汗研究较多,对林丹汗的研究在中外研究蒙古史和清史的专家中有所涉及。日本人和田清的著作《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收录17篇论文,其中第6篇为《察哈尔部的变迁》,对察哈尔蒙古的历史变迁有系统的论述。日本人萩原淳平《林丹汗一生及其时代》(涛海汉译文载《蒙古史研究通讯》第二辑)则对有关的察哈尔的历史及林丹汗一生的成就进行了阐述,后被其收入专著《明代蒙古史研究》当中。国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有很多,《蒙古族通史》、《内蒙古通史纲要》等史类专著,对林丹汗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察,薄音湖先生在《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的论文中、宝音初古拉教授在《察哈尔蒙古历史研究》、《明清时期察哈尔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好陈察哈尔研究》、《察哈尔脱卜察安》等专著中对察哈尔蒙古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对于察罕浩特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的资料比较稀少。近年来,学术界对林丹汗察罕浩特的的研究逐年升温。成立了中国蒙古汗廷文化研究会,学会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林丹汗都城察罕浩特的研究。金峰教授、那仁朝格图博士对察罕浩特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通过对察罕浩特的位置及其周围环境进行研究,确定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境内的白城遗址就是林丹汗时期的都城——察罕浩特。相关研究资料如《蒙古汗国最后都城林丹汗察罕浩特》、《阿鲁科尔沁旗白城明代遗迹调查报告》等,对确切地理位置进行了研究。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乔吉研究员首次提出了今辽宁省蒙古贞旗境内的察罕浩特遗址大概是林丹汗察罕浩特遗址的观点。但是后来他在汉庭文化研究会上自己主动承该观点因受到当时史料的限制有明显的失误。年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吴芝宽、昌戴等发表论文,认为今蒙古贞旗境内的察罕浩特遗址就是“林丹汗察罕浩特遗址”。但他们的观点被后来的那仁朝格图等学者们用年阿·玛·波兹德涅耶夫对辽庆州白塔蒙藏文碑文所作的拓片等有力证据一一否定。其实对林丹汗察罕浩特的研究建国初期就开始了。余元盒著《内蒙古历史概要》一书认为,“察哈尔汗主帐设在广宁直北之地,去明边一千余里。”广宁在蒙古贞旗境内的察罕浩特遗址西南只有一百余里。按照余先生的观点察罕浩特应该在今阿旗境内。 年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文化局都嘎尔从该旗的乌拉盖苏木老人赵德宝口中听说林丹汗曾在今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境内的阿巴嘎哈喇乌拉山旁建造“亚新察罕浩特”的传说后专程前来进行田野调查,考察了民间传说中的瓦其尔图察罕浩特遗址后首次报道了今阿旗罕苏木西十五里处阿巴嘎哈喇乌拉山城址就是林丹汗察罕浩特遗址的结论。主要根据有: ·当地蒙古民间老人都说相传这个故城遗址就是蒙古林丹汗居住过的察罕浩特,而且所在地的山名、城名都与蒙古文史书记载相吻合; ·从地理位置也与学界考证的林丹汗驻牧地一致; ·城址内有不少建筑物的遗迹、琉璃瓦残块等,与史书所记林丹汗崇信佛教、广建寺庙的记载吻合。 赤峰地方文化工作者敖·包音乌力吉、达木林苏隆、阿·胡图灵嘎、萨义宁布、额尔德尼等都曾证明都嘎尔报道的旧城址就是林丹汗察罕浩特遗址,考古工作者张松柏通过实地考察后也认为今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境内的白城遗址即林丹汗时期修建的都城。达力扎布、乌云毕力格、宝音初古拉等学者也利用赤峰档案馆藏蒙古文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对入清前的察哈尔万户驻牧地和清初和硕亲王额哲所属“察哈尔国”驻牧地作了有力的考证,都不约而同的证明了察哈尔万户的腹地带应在西拉沐沦河以北的阿鲁科尔沁旗境内。 年,蒙古汗廷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一百多位学者利用两天时间对察罕浩特的历史进行讨论,其结论是根据过去大部分学者们的观点和遗留史料、出土文物等多方分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今阿鲁科尔沁罕苏莫苏木城郭遗址应该是林丹汗的都城察罕浩特的遗址。根据多数学者的呼吁,年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把察罕浩特遗址的保护与发掘工作列入计划,将从4月份开始对其进行发掘和保护。 一、察哈尔蒙古 (一)察哈尔蒙古的起源 察哈尔名称由来已久,对它的词源的解释,有来源于波斯语、突厥语、蒙古语等不同方面的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蒙古国铁木尔策仁提出: “察哈尔之名称,该词来源于波斯语,可能通过栗特语融入突厥和蒙古语。一开始专指汗王宫廷为察哈尔,后逐渐转义命名汗王卫士、随从为察哈尔,最后成为可汗亲信和担负护卫军任务的部落群体的专有名词”。"[1]察哈尔早期的形成是成吉思汗赏赐给唆鲁禾帖尼别乞的可汗斡耳朵仆人群体。斡耳朵又被称作斡鲁朵、斡里朵,突厥一蒙古语ordo的音译,意为宫帐或宫殿,《辽史》载:“宫曰斡鲁朵”[2]。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契丹族,他们君主长期生活在没有城墙宫殿保护的宫帐之中,以车马为家,帐居野外时能随时的转移迁徙,所以其宫帐的构成、护卫、补给与管理都有一套与之适应的特殊制度。宫帐为九宫或九帐,也便是九斡鲁朵。《辽史》载: “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3]自辽太祖起,各帝及太后执政时都设有各自的斡鲁朵,作为独立的军事组织,有自身直属的军队和独立的经济来源。元朝的斡耳朵与辽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存在。而唆鲁和帖尼别乞则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夫人,后来便作为拖雷家族的主妇所受封的特殊领户被继承下来,世代归后妃私人所有。 北元初期的蒙古内部分裂,各部族间斗争频发,中央政权旁落,社会极度动荡,直到北元中期,蒙古社会才得以重新组合。在此过程中,以后妃的私人领户为基础,加上拖雷家族其它的传统领户所构成的庞大的政治群体逐渐形成。他们被命名为“察哈尔”,这一群体被统称为“察哈尔万户”,并且以北元可汗直属万户的身份、以统一蒙古为目的登上了历史舞台。 说到察哈尔蒙古,就不能不提及好陈察哈尔。好陈察哈尔的蒙古语意思为“原有的察哈尔”或“旧察哈尔”,其中包含“正宗察哈尔”的意思,是察哈尔万户中最为原始的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好陈察哈尔来源于唆鲁禾帖尼别乞嫁给拖雷时从嫁来的二百户克烈人以及拖雷死后可汗赏赐她的诸多家仆。后来随着拖雷家族汗位的变更,上层统治权利的不断变化,好陈察哈尔如同遗产一般被不断的继承, [1]铁木尔策仁《蒙古语词汇研究》乌兰巴托,年。 [2]《辽史●宫卫志上》。 [3]《辽史●营卫志●宫卫》。 使其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并发展壮大。《皇明北虏考》载: “众立卜赤,称亦克罕,亦克罕大营五,日好陈察罕儿,日召阿儿,曰把郎阿儿,曰克失旦,日卜尔报,可五万人,卜赤居中屯牧,五营环卫之”。[1]《皇明九边考》载: “北虏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边,兵约五万,为营者五,日好城察罕儿,日克失旦,日卜尔报,东营曰阿儿,西营曰把郎阿儿,入寇无常。近年虏在套中,以三关为出入之路”。[2]从这两段资料中可以大体看出在卜赤汗时期的察哈尔群体构成中,最基本的五个大营是五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总体建制由右翼、左翼、中央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的中央直属力量由三个独立单元组成,其中就包括好陈察哈尔。 察哈尔万户则以好陈察哈尔为核心,以及其他具有专有部落名称且各自有蒙古封建主台吉的若干蒙古部落所组成。元朝在与明朝的斗争失败后,元朝皇室的中央权利机构败退蒙古草原,又恢复了昔日蒙古汗国时期的部落组织。一些直接充当元朝皇室各类专业机构人员和拖雷家族的直属传统领户都与察哈尔万户的来源有关。例如: 察哈尔万户的克什克腾部源于元代的怯薛军; 乌珠穆沁部与元朝皇宫中的酿酒色目人有关;(东北君:乌云毕力格先生考证,乌珠穆沁应为“占星家”) 苏尼特部的来源与皇宫宿卫有关; 浩齐特部与元朝皇帝直属原有的旧侍从有关等。 从达延汗开始的历代蒙古可汗都对自己的子孙进行了分封,这些分封也导致部分部落开始脱离察哈尔。在卜赤汗时期的五个大营也随着发展和变化逐渐演变为九部,《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一年(公元)闰五月戊辰条: “天爵之来也,其言虏情甚详,谓虏酋小王子等九部咸住牧青山,艳中国纱段,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两端,抢虽获有人畜,而纱段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市完”,[3]其中对九部进行了记载。而九部这一察哈尔万户的构成形式则一直保存到土蛮汗时期。 (二)察哈尔蒙古的变迁 卜赤汗时期的察哈尔万户变迁与他的政治、军事活动紧密相连。兀良罕万户的叛乱、蒙古右翼强盛的俺答汗使他不断的转战南北,而察哈尔万户也随他一起不断迁徙。达延汗后,卜赤汗继承汗位,率领部分蒙古左翼万户南下,其中包括察哈尔万户,开始对蒙古右翼施加军事压力。遭受了达延汗征服战争的蒙古右翼,生产生活都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察哈尔等蒙古左翼万户带来的战争恐惧感依然 [1]郑晓《皇明北虏考》正德间条,《吾学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2]魏焕《皇明九边考》卷六“边夷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 [3]《明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影响着蒙古右翼,使其不敢与强大的卜赤汗进行抗争。《万历武功录》载: “(正德)十六年,虏寇花马池,时虏可汗阿著死,部人立故阿尔伦台吉之长子卜赤,号亦克汗”。[1]正德十六年即公元年,卜赤汗顺利的继承了汗位,这一次的率军南下是卜赤汗时期的察哈尔南迁。公元年,漠北兀良汗万户乘卜赤汗南征内部空虚之际,对喀尔喀右翼别速惕部进行袭击,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叛乱。卜赤汗此时为了稳定后方,选择了暂时在漠南驻扎放牧,并开始组织左翼和右翼的军事力量对兀良汗的叛乱进行镇压。《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一年(公元)六月戊戌条: “北虏之众,凡有三窟:一屯河套,近延绥;一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一屯北口青山,近宣府”。[2]河套地区一直为鄂尔多斯万户的根据地,卜赤汗在漠南的放牧区域则为威宁海子、北口青山地区,位置处于现今的以集宁为中心的呼和浩特以东,大同、宣化长城一线以北地区。直到公元年左右翼和兵讨伐兀良汗获得成功,南下的察哈尔才从漠南迁移回漠北故地。平定叛乱后,蒙古左右翼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卜赤汗对自己的直属察哈尔万户重新进行了分封,但是其分封措施引起了部分部落的不满,一些察哈尔部落转而投靠了蒙古右翼。而蒙古右翼借平定兀良汗叛乱趁机壮大自身势力,在卜赤汗再次南下想采用武力解决蒙古右翼却为时已晚,被迫与右翼俺答汗修好,承认其在蒙古右翼的统治地位,随后又匆忙北迁,回到漠北的根据地。《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六年(公元)六月癸巳条载翁万达报告说: “今虏酋俺答、把都,久驻大边威宁海子一带,套虏吉囊一枝,亦复移营东渡,声势重大”。[3]从中可以看出,在卜赤汗北迁后,俺答汗右翼马上占据了北迁察哈尔的所有驻地,至公元年,蒙古左翼在漠南的驻地已不复存在。《黄金史》载: “卜赤汗在位二十四年,羊儿年在照图朗山去世。”[4]卜赤汗于公元年在无奈和痛恨中去世。 [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汗列传,正德条。 [2]《明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3]《明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4]《黄金史》P。 公元年达赉逊汗即位,他选择了继续隐忍漠北,躲让蒙古右翼俺答汗的锋芒,并做着南征的准备。《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九年(公元年)十二月丁丑条: “达虏部落皆在宣大边外。然小王子一部独处东偏,万一有警,将经下辽东、薊,不由宣大。"[1]说明此时察哈尔已经开始了南迁。没过多久,他开始了一项宏伟的计划,他率领蒙古左翼军队大举进攻山阳万户,山阳万户是指明朝称之为的“兀良哈三卫”。为避免和蒙古右翼的军事接触,达赉逊汗选择了驻牧于蓟、辽地域,即现今的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地区,在与明朝有了边境接壤后,借助已经被其征服的兀良哈三卫开始与明朝通贡,得到明朝的市赏。此次察哈尔南迁到潢水以北地区(西拉木伦河以北),其中心地带以现今赤峰市巴林左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为核心,北至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全境,东至通辽市扎鲁特旗的广大地区。 土蛮汗时期开始了对明朝采取强硬的政治策略,开始借助武力以达到与明朝全面贡市的目的。土蛮汗即位以后接连对明朝的边境进行侵扰行动,给明朝蓟、辽边境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辽夷略》载: “自宁前而东,我边地渐广,则广宁、锦、义诸堡矣,距塞外者皆朵颜诸部也。其酋曰土蛮憨,号老王子。子九,自长男扯臣憨而下,曰委正黄台吉,曰额参台吉,曰锁迷台吉,曰歹青台吉,曰琵琶台吉,曰莽官儿台吉,曰卜言大台吉,曰桑阿儿赛台吉。今诸酋皆虎墩兔憨约束之。牧地直广宁,去塞十余里,而市赏皆广宁镇远关。扯臣憨长男曰莽骨速台吉,即虎墩兔憨之父也,二子,一为憨,约束诸部。而次曰粆兔黄台吉,兄弟约兵三万余骑。次男曰毛起炭,存,而有一子曰脱脱亥,其骑亦有五千。此莽骨速之派为独盛而制诸部也。虏中称憨如称帝。委正故,二子,长伯言,次伯言大,而约兵三千余。额参台吉故,仅一子曰召克太,绝矣。锁迷之子长麦力根,次哈大,亦拥骑二千余。歹青之子二,曰孛赖,曰黄台吉,俱在...亦兵约二千余骑也。琵琶之子曰克什兔,曰阿败,约兵千骑耳。其莽官儿尚存,而有子曰伯言兔,亦约兵千余骑。卜言太存,有三子,长色令,次拱赤,三把兔儿,而兵数亦与琵琶同。桑阿儿寨存,生子四....拥骑三千余,而视莽官、琵琶、卜言太三部差雄矣。计土蛮之派凡二十一枝,俱帝虎墩兔憨。憨兵不下三万,而合诸酋兵又几二万,是以为土蛮之种强矣。”[2]从以上的数字中就可以看到仅土蛮汗子孙的察哈尔本部(即好陈察哈尔)军事势力就能达到控弦五万余骑,察哈尔在士蛮汗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土蛮汗时期,明朝与察哈尔的关系都处在敌对状态,动辄刀兵相见。一方面明朝拒绝开放辽东贡市,但财力枯竭,将士毫无斗志;一方面蒙古政权经济形式单一,但是兵强马壮。土蛮汗是在蓟辽战线上度过一生的威震辽东的枭雄。《万历武功录》载: [1]《明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2]《辽夷略》。 “土蛮老而厌兵,边患稍戢,久之,以狗马病死。子卜言台周嗣..土蛮,故胡元裔,又俺答君长,意中独恋恋贡市事二十余年,乃卒不可得,老死矣”。[1]在土蛮汗晚年,虽然对明朝的战争稍微削减,但是依然没有达到全面贡市的目的。历经几代人的发展,虽然每任大汗为了蒙古统一都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历史大局依然无法挽回,蒙古各个部落依然处在各自为政的局面之中。到林丹汗即位时,虽然他是整个蒙古名义上的大汗,可他的政令只能在自己统治的察哈尔部中得到施行。他的目标是恢复大汗权威和统一蒙古,可他的命运在他登上汗位时起,就注定是会以悲剧而告终。 [1]《万历武功录》土蛮列传下。 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广宁镇境图》 可见当时马市的位置 二、林丹汗与察罕浩特都城 (一)林丹汗时期的察哈尔蒙古 林丹汗时期的蒙古处于分裂状态,漠南蒙古包括: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永谢布部、察哈尔部、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部,各部虽然名义上承认了林丹汗的蒙古大汗的位置,但实际上都凭借着各自的军事实力各自为政。留守漠北的鄂托克部只承认他为察哈尔一部之汗,对蒙古名义上的大汗拒绝承认。漠西的卫特拉部早在达延汗时便因地理及历史等因素自成一体。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的藏传佛教更是在蒙古社会内部引发了诸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此时的蒙古周边,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各阶级间、各民族间的矛盾突出,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北方的李自成起义,南方的张献忠起义都沉重的打击着明王朝的统治。随着明王朝的衰败,为一直与明王朝对抗的察哈尔部提供了崛起的绝佳时机。 在军事上,蒙古与明朝的边界战争逐渐减少,使得与明王朝斗争百年的蒙古政权有了喘息的机会,在明朝忙于内部的斗争时,减少了对蒙古各部族的分化瓦解力度,有利于林丹汗展开对蒙古各部落的统一。而且为了抗击日渐强大的女真政权,明朝不仅对察哈尔蒙古开始通贡,还对其许以高额的岁币,这就增强了察哈尔部的经济实力,也为林丹汗能快速的发展自身的军事实力提供了物质条件。东北的女真政权也在逐渐的发展壮大,曾经受到明朝压制和剥削的女真族,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最终完成了统一,其势力开始向辽东地区发展。女真的发展壮大直接威胁了蒙古东部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女真的扩张对蒙古部落的正常游牧生活和蒙古与明在东北的互市产生了威胁,使蒙古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女真与蒙古间的矛盾凸显。林丹汗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据《蒙古源流》记载: “长兄林丹把都儿台吉生于壬辰年,于甲辰年十三岁时即位,以忽秃图合罕之称名扬四方”[1]幼小的林丹汗在甲辰年即公元年继祖父布延彻辰汗之后承袭了蒙古大汗位,汗号为呼图克图合汗。林丹汗即位时年仅十三岁,无法操控大局,. “幼憨嗣立,柔弱未为”[2][1]乌兰《蒙古源流》辽宁民族出版社,年。 [2]《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兵部尚书奏文。 在经历了10年的隐忍之后,林丹汗对明用兵的军事行动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林丹汗亲率十万大军,连续三次进入明朝边境,频繁的在广宁至锦州数百里长的战线上进行出击。此次战役声势浩大,第一次率十万十七日攻克辽东重镇广宁;第二次率六千骑兵二十日攻克锦州;第三次率六万二十二日攻克大安堡。这使明朝官兵惊呼: “虎墩兔憨为虏中之名王,尤称架骛。”[1]林丹汗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迫明朝恢复贡市。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建立“金国”,并开始了对辽东明军的军事行动,明朝在此时恢复贡市也有希望通过林丹汗来制衡努尔哈赤的目的。 在与明朝恢复贡市的同时,林丹汗开始了对蒙古各部族的统一战争,他的目标就是游牧于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选择科尔沁部作为第一目标除了战略目的以外,应该有个人的仇恨掺杂其中。在林丹汗先辈土蛮汗时期的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中,科尔沁部就有过背叛盟约的行为,土蛮汗曾发兵征讨。《万历武功录》载: “其明年冬,八家寨、夹河山城、苇子谷酋长汪住、内英哥、锁落可赤、把其三、把儿太、宁公提等,从阳明台入。是时,速把亥、委正、抄花、好儿趁、者儿得聚羊场河。与土蛮未合,相攻杀。顷之,好儿趁与土蛮讲和...者儿得亦讲和”。[2]此后,在军事实力的畏惧下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科尔沁保持着与察哈尔的联盟关系。在林丹汗即位初年,缺乏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撑,各部落只能自寻出路,本身就有这很强自主性的科尔沁更加的远离了察哈尔汗的控制。而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对明朝的进攻,增强自身的实力,对蒙古各部采取了分化、瓦解、拉拢的政策,对科尔沁部更是积极的争取,导致了林丹汗与科尔沁部的关系更加恶劣。为了打击科尔沁部、震慑蒙古其他部族并希望遏制后金政权的势力扩散,林丹汗于公元年亲自率军征讨科尔沁部,对格勒珠尔根城(今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西南)展开围攻。林丹汗久攻不下,加之后金援兵即将到了,无奈之下选择退兵。林丹汗的这次军事行动目的是收复科尔沁部,是进行蒙古统一的关键一一步。对林丹汗而言,行动成功,不仅能收复科尔沁部、抵御后金的渗透,更能威慑其他的蒙古部族,有利于统一蒙古的进行。对后金而言,能够彻底把科尔沁部拉入自己的阵营,更能削弱林丹汗势力、增强自身力量。林丹汗这次行动的失败使自己与后金的斗争开始处于下风。林丹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和对内部所采用的残暴手段,虽然使察哈尔部势力在短期内得到了一定的增强,但却严重的影响了自身的威信,失去了蒙古部族的民心。左翼蒙古的首领们对林丹汗多有抱怨,如额尔德尼杜棱洪巴都鲁台吉在天聪三年(公元年)九月十八日 [1]《明实录》万历四十五年五月辛未条。 [2]《万历武功录》土蛮汗列传。 致皇太极的信中写道: “因这个罪恶的察哈尔汗性情暴躁,对众人危害极大,即使是宗族至死至穷绝不会归附他的缘故就在这里”。[1]林丹汗的行为使本来散沙一盘的局面变的愈加不堪,恐怖的政策促使科尔沁与女真最终结盟;在后金对内喀尔喀部进行攻击时,林丹汗非但没有出手相救,反而兼并其部族人口。至此,几个影响力较大的左翼蒙古部族覆灭、科尔沁加入了后金阵营、察哈尔内部矛盾却不断激化,这说明林丹汗在西迁之前的对内行动是彻底失败的。 (二)察罕浩特都城的修建 17世纪的前期,林丹汗建造了察罕浩特(汉语意为白城),全称为瓦齐尔图·察罕浩特(汉语意为金刚白城)。这一时期的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有关于林丹汗建造都城的记载。《蒙古源流》载: “林丹汗于丁巳年二十六岁时拜见了萨思迦答察沙尔巴虎督度,再次接受了精深密乘的灌顶,修建了宏伟的殿宇和金刚白城。“林丹汗在城中兴建了供奉释迦牟尼像的众多庙宇,一个夏季当中即迅速建成,寺内的众佛像也全部完工。”[2]蒙古文史书《金轮千幅》也记载了建造金刚白城的地点以及城内建筑分布状况: “在阿巴嘎哈喇乌拉山阳建造了察罕浩特城和金顶白寺,并将八鄂托克察哈尔土蛮(万户)分左右翼三万户,右翼三万户由却如斯塔布囊来管理,左翼三万户由虎日呼纳克塔布囊来管理。”[3]林丹汗对察罕浩特都城的修建主要基于军事、政治、宗教三方面进行的考虑。察罕浩特城坐落在大兴安岭南麓,为丘陵草原地带。城址南有河床一道,现在已经干涸,滴水皆无。城址南有察干花山、得勒图大坝、哈拉少楞、呼和沙楞多座山峰。城址北有广袤的草原,再向北有阿巴嘎山、白音胡舒山,山北为白音温都苏木。城址北隔阿巴嘎山、牦牛大坝与马呢吐古城相对,相距约10公里。城东的一道山谷成为蒙古高原通往松辽平原的天然通道,在对外的经济活动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从察罕浩特往北可以迅速的通达漠北,保证了对漠北蒙古的控制,使其有一个稳定后方,还可以控制呼伦贝尔、科尔沁等处的大面积的天然优良牧场,有利于游牧的蒙古部落发展壮大自身的实力。从察罕浩特向西,有于蒙古右翼之间的巴林、克什克腾等地作为其间的战略缓冲,对强大的林丹汗来说又是对 [1]希都日古《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与蒙古文文书档案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年。 [2]乌兰《蒙古源流》辽宁民族出版社,年。 [3]乔吉校注《金轮千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 蒙古右翼用兵的桥头堡。察罕浩特的位置向南到明朝的边境与向西到后金的边境距离相近,林丹汗可以做到在对明朝进行近乎勒索的要求贡市的同时,又能随时调兵对后金形成军事威胁,这就保证了林丹汗可以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做到发展自己势力、保证三方平衡的军事目的。 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逐水草而居,部落都有非常强的流动性,他们的生活习俗决定了无法像中原的汉民族的农耕社会一样去修建众多的大型城市。在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也出现过如渤海城、统万城等,最终都毁于刀兵。因为城市无法移动,又是财富、人口的聚集区,容易被敌对势力所觊觎,只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政权时,才能保证完整城市的长期存在。林丹汗对察罕浩特的修建是其对外展示其实力的手段的一种,体现了其作为蒙古大汗的权威,占据着政治地位的制高点,在对周边各蒙古部落的政治活动中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林丹汗一生对于佛教的崇拜促使了蒙古左翼地区的藏传佛教的传播,在蒙古文化的发展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公元年,林丹汗接受了四世达赖派驻蒙古地方管理教务的迈达理呼图克图、卓尼绰尔济等黄教喇嘛等人的格鲁派法戒,蒙文史籍《黄史》记载: “从迈达理法王卓尼绰尔济等人承受精深密乘之灌顶,扶崇佛法”。[1]公元,二十六岁时又从西藏萨迦派高僧夏尔巴呼图克图处承受了精深秘乘灌顶。公元-公元年,在林丹汗的指令下,译经师贡嘎斡节儿等人将《甘珠尔》经进行了蒙古文翻译。虽然《甘珠尔》经的部分内容在以前就做了蒙古文的翻译,但林丹汗组织的这次译经活动除了对以前的蒙古文译文重新做了校对外,更是将其所缺的内容进行了补译,最终编成的《甘珠尔》经共计函,这就是蒙古史上常说的“林丹汗金字《甘珠尔》经”,其被称颂为: “蒙古人最大的一项文化成就,不仅对佛教传播有极大的贡献,就是对整个蒙古人的文化,尤其是书面文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历史性的重要影响”。[2]林丹汗更是修建佛寺庙宇,希望通过增强察罕浩特在草原上的宗教地位进而协助其进行统治,为统一蒙古进行宗教上的优势。 对于察罕浩特都城的具体修建过程已经无法从史料中的到太多的了解,但作为当时蒙古部族中有最强力量的林丹汗,修建都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现存遗址上还能感觉出当年察罕浩特当年的繁华景象。 [1]格日乐译注《黄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年。 [2]乔吉《蒙古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 ligdanhutuktuhaan 林丹呼图克图汗 三、林丹汗后期的察哈尔部 (一)察哈尔部西迁 《明实录》关于林丹汗察哈尔部的西迁载: “一旦拔帐而西,骚动宣、云已逾半载”[1]可以看出公元年10月时林丹汗率察哈尔本部的西迁声势浩大。 “是月,插汉虎墩兔憨与习令色盟于归化城,以合犯气喇嘛守之,东行降兀慎、摆腰、明暗等酋”,[2]表明此时的林丹汗察哈尔部已进入了明朝宣府、大同以北的哈喇嗔、土默特两部的驻地。 林丹汗对明朝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明朝的贡市、加大与明朝边境的经济贸易,可是在广宁被后金所得后,明朝彻底的失去了对辽东的控制,而林丹汗也无法继续与明朝进行互市,并且其更加感觉到了来自后金的压力。此时的蒙古右翼哈喇嗔诸部得市赏十八万,卜石兔得市赏十一万,这是自视正统且贪图利益的林丹汗所不能接受的, “吾亦欲得金印如顺义王,大市汉物,为西可汗,不亦快乎?”[3]“虎墩兔新强,拥众数万,而板升富庶,甚习内地。插汉原在辽东,领赏卖马必由两哨,既与俺答积衅数世,会素囊死,卜石兔有其地,然幼且弱,插汉遂倾巢而西,以旧地让建州”。[4]林丹汗通过军事行动击溃了蒙古右翼各部族,接管了右翼部族的互市口岸,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达到了他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在林丹汗占据宣府、大同的边外之后,立即拥兵张家口, “声言欲得卜石兔市赏”[5]年开始西迁,林丹汗接连击败哈喇嗔、土默特和鄂尔多斯等右翼部族,其军队横行于东起辽河,西至鄂尔多斯河套的大面积区域。林丹汗在西迁过程中用了较为残酷的手段来对付蒙古右翼各部,由于蒙古民族游牧生活的特性,各蒙古右翼只是被驱逐出自己的驻牧地,并未彻底的被林丹汗降服,仍与之继续为敌。在林丹汗独享贡市之利后,并没有得到满足,迫不及待的对明朝提出市赏要 [1]《崇祯长篇》崇祯元年六月癸卯条,台湾《明实录》本,年。 [2]《崇祯实录》天启七年十一月癸巳条,台湾《明实录》本,年。 [3]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西人封贡》中华书局,年。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插汗寇边》中华书局,年。 [5]《国榷.卷八九》崇祯元年四月庚戌,中华书局,年。 求,也表明了其要独享与明朝互市利益的目的,这正是此时林丹汗率察哈尔西迁的主要原因。而明朝方面认为察哈尔向来“名为盟友,实乃挟赏”,加上西迁后对后金政权牵制作用的减弱,最终拒绝了林丹汗的要求,林丹汗又对明边进行了袭扰掠夺,导致了察哈尔部与明朝间关系彻底破裂。 林丹汗的西迁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长期的征战却消耗了自身的军事、经济的实力,使原本较为富足的蒙古右翼实力大伤,在内部政治上处于孤立的状态,彻底消除了蒙古内部统一的可能,客观上为后金西征创造了条件。 (二)林丹汗的败亡 察哈尔部的存在严重阻碍着后金对明朝的军事行动,分裂的蒙古也不利于后金对明朝用兵时其后方的稳定。公元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皇太极调遣已归附的蒙古部族中的喀尔喀、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向察哈尔部发动进攻,其后又集中喀喇沁、奈曼等部,亲自率军西征再次击溃察哈尔部,并占领了西拉木伦河和克什克腾区域。公元(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皇太极再次亲征。面对后金强大的军事攻势,林丹汗被迫向西退逃,察哈尔部众大部分溃散或投降。公元年(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公元年(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其子额哲献上传国玉玺并率残部向后金投降。随着后金对中国的统一,北方战乱逐渐平息,察罕浩特失去了其在与后金对峙时期的军事价值,加之各种主要生产生活活动都逐渐向平原一带转移,察罕浩特的人口也随之向南迁徙,人口的逐年流失,最终导致了察罕浩特的废弃。 林丹汗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策略方针的失败早已决定了他败亡的命运。林丹汗采取了的政策为“先处里,后处外”[1],主要以处理内部事务为主。其对蒙古各部主要采用强硬的军事暴力手段,无法取得蒙古各部的信任,达不到统一团结的目的,反而削弱了蒙古内部的民族凝聚力,使蒙古民族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阻碍了蒙古社会原本就单一落后的经济的发展。其对藏传佛教的狂热崇拜使得宗教势力迅速扩张,严重削弱了大汗的统治权威,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加之无休止的、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更是对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在明朝和后金两个强大政权之中摇摆不定,虽然得到了短期的利益最大化,但却失去了作为独立国家应有的威信。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林丹汗最终走向失败,而崛起的后金政权开始了对中国的统一。 [1]《崇祯长篇》崇祯元年七月,台湾《明实录》本,年。 hvwaliyasunenduringgehan 花喇荪恩都灵格汗-皇太极 四、察罕浩特遗址 察罕浩特遗址即白城遗址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属罕苏木查干浩特嘎查管辖。南距旗政府所在地天山镇75公里,东距苏木所在地巴彦呼舒7公里,西距查干浩特嘎查2公里。在这一带的遗址内,包含了同一历史时期而不同阶段修建的三座城市遗址和两处墓群,以城址为中心的区域内分布着大面积的村落遗址。 (一)中心白城遗址 白城是这一区域内最大的中心城市,规模宏大,各个建筑的布局主次分明,构造严谨。城内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形成回字形的布局,城郭南北短而东西长。 1、外城 外城的城墙南侧利用山脉形成天然的保护,部分地段补充石墙,其余三面夯土筑成。整个外城城墙呈长方形,东北角和西北角筑有角楼,建有南北两座城门。东城墙长米,西城墙长米,北城墙长米,南城墙的石城墙地带处于东南、西南两座棋盘山之间基宽2米,顶宽1米,残高1.7米,正中建有宽10米的南门。外城东南角的东棋盘山因山顶刻有蒙古象棋棋盘得名,分布了4座大型殿基址。I号殿基址位于山阳部,长方形,边长14米,宽8米,残高1.2米,散布了大量的绿色琉璃瓦。II号殿基址位于山项一个大平台上,正方形,边长12米,残高2米,散布了沟纹砖和绿色琉璃瓦。Ⅲ号殿基址位于山顶部,正方形,边长8米,残高3米,散布绿色琉璃瓦。IV号殿基址位于山背阴坡上,长方形,殿基四边为石块砌垒,长10.8米,宽6.9米,残高1.4米,散布了灰色素面砖瓦。山西侧的岩石上一些险峻地段开有圆形孔洞,共有24个,估计为插栏杆所用,以防止人滑落,在上山道路转弯处两侧,各有直径37厘米、深18厘米的圆孔和直径22厘米、深10厘米的方孔作为旗杆的插孔。 外城内的遗迹分布较少,分布在东西两翼的建筑多为石块砌垒的小型房址,排列十分有序。地表散布了一些石白,估计东西两翼区域所居住的是专门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住宅区。较大的建筑址分布在外城的五处不同地段,第一处在通往内城南门的大道两侧各有一处相对的方形夯土台基,边长12米,残高4米。第二处南门西侧的方形院落以夯土围墙,南墙建有一门,院墙东西33米,南北41米,北墙处有一排长方形房址。第三处在外城南部有8座一字排开的长方形房址,边长20米,宽6米。第四处在西棋盘山背阴坡处,有3处长方形殿基址,长12米,宽6米,残高1.4米,一字排开。第五处在外城西南部,长方形夯土台基,长12米,宽8米,残高0.7米。 2、内城 外城中心的内城,城墙高大,防御设备完善。城墙呈正方形,边长米,东部南段保存完整,其余部分都已经坍塌。南段城墙墙基底宽12米,建筑时采用了大块的岩石,顶宽6米,高8米,顶部马道铺路选用河卵石。内城仅开有南门,并建筑环形瓮城,瓮城直径22米,门址宽10米。内城四角设有正方形角楼,突出城墙5米,高出城墙2米。 内城的建筑多为宫殿,共分布了7座大型夯土台基,主要宫殿处于后部。中轴线上建有3座大型配殿,其后部的中心部位建有最大的宫殿建筑,其建筑于一个巨大的夯土台基上,台基中间为正方形,两侧为长方形,前方中间为宽大的台阶,大殿总长80米,中心台基宽34米,高4米。在中心台基之上建有长方形的宫殿,柱础和方形铺地砖保存完整,长22米,宽15米。侧殿为正方形,边长8米。在大殿前方的两侧各筑3座配殿,长方形的台基为方形石块砌筑,长19米,宽17米,面向大道建有台阶,其上的宫殿建筑已被破坏。在所有的宫殿处均有大量的绿色琉璃瓦残片和素面灰砖瓦残片,估计宫殿主要由琉璃瓦和砖瓦混合构建。外侧配殿和中央大道西侧各有水井,现已坍塌,西井坍坑较大,直径15米,深4米;东井坍坑较小,直径6米,深4米。坍坑内均发现有砌井所用的方形石块。在内城南部有一处大型的方形院落,土墙围筑,东西墙41米,南北墙36米,墙基底部宽3米,残高0.4-1米,顶宽0.6-1米。院落西南有井一眼,也已经坍塌,坍坑直径10米,深2.1米。在内城东南角处有一处大型院落,背靠东、南城墙,东西长34米,南北宽18米,宽2米的小门开设于北墙中央。院落中间的高大方形夯土台基边长10.5米,高达8米,顶端与城墙平齐,上部散布砖瓦和柱础,说明顶部曾经有过建筑物。 3、遗物 琉璃板瓦,见于内城中央的大殿基址,红色胎,胎质坚硬细密,外施绿釉,残长12厘米,最大半径19厘米,厚2厘米。 砖瓦,内外城共发现不同规格的长砖,黑灰色,质地坚硬,杂质较多。 缠枝牡丹纹雕砖,残,长方形,主体图案为浅浮雕缠枝牡丹花,呈半圆形横带状,残长14厘米,高14厘米,厚4厘米。 覆莲纹雕砖,半圆形,底平上圆,上雕浅浮雕覆莲,莲叶呈翘边重叶形,直径17厘米,高8厘米,厚4厘米。 蕉叶纹雕砖,半月形,底残,边缘两侧雕对称蕉叶,蕉叶上端沿外缘曲边内弯,残高12厘米,宽20厘米,厚15厘米。 菱形几何纹雕砖,上雕阴刻相互交叉的同心菱形图案,残长14厘米,宽9厘米,厚4厘米。 石臼,位于外城西部,半圆状,白色花岗岩制作,上部平台磨光,下部粗加工打磨,平台呈圆环宽边,中间为圆锥形臼,高70厘米,宽60厘米,臼孔直径40厘米,深25厘米。 石磨盘,位于外城南部西侧,为磨盘上部,形如外缘高中间平的盆形,表面刻线处理,凿刻成相互斜角平行线纹,中间刻有圆孔,磨面刻七组斜平行线纹,直径80厘米,厚19厘米。 石碾,位于内城南部,圆柱形,半残,花岗岩制作,两头大小不一,一端中部刻有方孔,表面刻横槽线,残长70厘米,最大直径58厘米,最小直径50厘米。 (二)东白城和西白城 东白城城址位于白城城址东部偏北2公里,建在平坦的草原上,呈长方形,南北长米,东西宽米,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城墙基底宽10米,顶宽4米至2米,高2米至0.7米,夯土层厚0.1米。南门宽7米,东、西门宽5米。城内建筑遗迹较少,中心有大型夯土台基,略呈正方形,南北长18米,东西宽16米,高2.1米,台基散布大量绿色琉璃瓦和灰色砖瓦,在该台基的北部有俩座相对应的夯土台基,东西长40米,南北宽14米,高1.7米。 西白城位于白城外城西侧中部,城址西部被白城外城西城墙打破,表明该城时代要早于白城。城址呈长方形,城墙南北长而东西短,城墙早已坍塌。内外城均开有南门,外城城墙低于内城城墙,西段和北段保存较好,东半部处于白城外城内,破坏较为严重。城墙东西宽米,南北长米,墙基底宽8米,上宽1米至0.4米,高2米至0.6米,南北均宽9米。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城墙比较高大,东西宽80米,南北长米,城墙基底宽10米,上宽0.8米至2米,高1米至3米,夯土层厚0.8厘米至1厘米,南门宽8米。内城正中偏北和紧靠北城墙处一前一后两座大型殿基址,前大殿为主殿,夯土台基呈正方形,边长35米,台基高2.3米,中央的大型殿基址呈正方形,边长12米,散布许多绿色琉璃瓦和方形花岗岩柱础石。后大殿台基址比前大殿略小,方形,台基边长12米,高2米,台基上建筑址早已不存,散布绿、蓝两色琉璃瓦饰件残片。 结语 本文首先先对林丹汗在位时的主要军事力量来源蒙古察哈尔部进行研究,了解察哈尔部的起源及其主要的变迁过程。察哈尔部从被成吉思汗赏赐给拖雷家族开始,到蒙古帝国从中原地区退守长城以外的蒙古地区为止,察哈尔仅仅是拖雷家族后妃的斡耳朵仆人,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其这一时期的历史不见经传,处在被蒙古社会遗忘的角落。而北元时期,为了恢复曾经辉煌的统治,在与明王朝的连年战争中,可汗数百万的直系军队被消耗殆尽。随着可汗势力的消耗,各部族的势力开始崛起,北方的蒙古社会陷入战乱、分裂。而察哈尔这一大汗身边的忠实仆人,继承了怯薛军忠诚、勇敢的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大汗身边的中坚力量。依靠察哈尔部崛起的林丹汗,能在与后金、明和各蒙古部落的斗争中坚持30年,就是察哈尔坚韧顽强的见证。 林丹汗在位期间,正处于后金和明王朝斗争激烈的时刻,在夹缝中获得了使蒙古部落崛起的有利时机,林丹汗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为统一蒙古做着不断的努力。强大起来的林丹汗修建了自己的都城察罕浩特,对林丹汗来说察罕浩特的修建从政治、军事、宗教各个角度衡量都有非常必要的因素。树立大汗权威、压制蒙古各部、扩大藏传佛教影响,可以想象察罕浩特内的林丹汗在巅峰时期所拥有的势力是多么的强大。 由于经济的原因,为了与明朝互市,林丹汗选择了率察哈尔部西迁,其统治也开始走向终点。西迁过程中林丹汗发动了对蒙古其他部族的战争,这次战争没有起到统一蒙古各部的效果,反而因林丹汗的残暴使各部首领对其离心离德,加剧了蒙古社会内部各部族间的矛盾,其军事、经济的实力更是不断的遭到削减。林丹汗的这次西迁为后金征服蒙古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其统治的灭亡写下了伏笔。 在林丹汗死后,后金政权征服了蒙古各部族,稳定了后方,为南下与明王朝作战打下了基础。随着蒙古地区的权利转移,林丹汗曾经的都城察罕浩特也失去了其作为统治中心的地位。虽然察罕浩特未遭受刀兵之灾,但随着后金对明王朝作战的胜利一直到大清统一中国,当地主要的生产生活活动逐渐的向南发展,当地居民开始陆续南迁,随着时间的流逝,察罕浩特最终荒废。 察罕浩特早已没有高大的宫殿建筑,只能从散落的琉璃瓦中感觉到曾经的辉煌。以前还会有附近的一些村民到遗址处挖掘完整的石块以供自家建房所用,导致遗址遭到了破坏。现在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已顺利的开展,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在这处遗迹中感受到历史中消失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年. [2]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年. [3]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年. [4]明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年. [5]崇祯长篇[M]台湾:《明实录》本,年. [6]崇祯实录[M]台湾:《明实录》本,年. [7]满文老档[M]北京:中华书局,年. [8]满洲实录[M]民国二十三年重印本. [9]清初史料四种●辽夷略[M]台北:进学书局,年. [10]郑晓.皇明北虏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年. [1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M]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本,年. [12]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年. [13]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年. [14]朱凤,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 [15]乔吉校注.金轮千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 [16]格日乐译注.黄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年. [17]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年. [18]希都日古.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与蒙古文文书档案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年, [19]乌云毕力格.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 [20]札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年。 [21]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年.[22]蒙古民族通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年。 [23]乔吉.蒙古佛教史-北元时期[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24]胡和温都尔校注.水晶念珠[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25]达力扎布.蒙古史纲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 [26]乌云毕力格.蒙古史纲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27]薄音湖.达延汗生卒即位年考[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年第4期. [28]薄音湖.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J]蒙古史研究,年第5辑. [29]薄音湖.北元与明代蒙古[J]内蒙古大学学报,年第1期. [30]王雄.察哈尔西迁的有关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年第1期 [31]戴鸿义.论林丹汗的败亡[J]社会科学辑刊,年第5期. [32]香梅.论林丹汗先处里后处外政策[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年第5期.[33]宝音初古拉.察哈尔蒙古历史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年. 推荐: JeanFranoisGerbllon鞑靼行纪9 年吴文藻笔下的蒙古包丨《北平晨报》刊载 包玉林:论朵儿边部的族源与族称 程嘉静倪晓华丨蒙古汗国斡耳朵的驻营形式及内部陈列 察哈尔扎萨克旗考 达力扎布:察哈尔林丹汗病逝之“大草滩”考(上) 达力扎布:察哈尔林丹汗病逝之“大草滩”考(下) 明珠尔:巴尔虎蒙古人从巴尔古真迁居察哈尔的考述 乌云毕力格:丝路沿线的民族交融——占星家与乌珠穆沁部(上) 乌云毕力格:丝路沿线的民族交融——占星家与乌珠穆沁部(下) 阿音娜N·哈斯巴根: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以雍和宫档案为例 吕文利:明末清初蒙古诸部试图建立“政教二道”中心的实践(上) 吕文利:明末清初蒙古诸部试图建立“政教二道”中心的实践(中) 吕文利:明末清初蒙古诸部试图建立“政教二道”中心的实践(下) 谢光典:蒙古袭来时的西藏掘藏师:咕噜搠思旺(Guruchosdbang,-)的授记与教戒 蒙古丨哈拉和林3D复原图 晓克:“土默特”名称再议 刘蒙林:康熙皇帝出巡归化城述论 蒙林:清太祖时期后金与索伦部的关系 年,晚明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 姑茹玛:《北喀尔喀与爱新国的最初接触及其影响》 杜洪涛:靖难之役与兀良哈南迁 明代丨汉人与女真人的马市贸易 东北利亚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