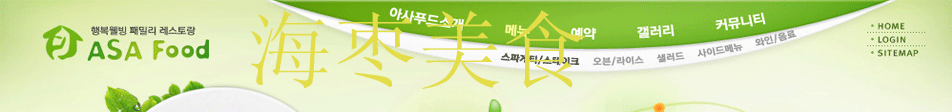|
四、商业网点广宁村里有百货、副食、饭馆、储蓄所、粮店,理发馆、澡堂子(浴室)、奶站、缝纫部、邮电所、煤球场、修鞋铺、自行车修理铺、废品回收站,以及流动的磨剪子磨刀、锔盆锔碗、修理搓衣板、修理竹帘子......真是全了。村里唯独没有照相馆,我们那时候照相,都得步行三公里,到北辛安大街的石景山照相馆,这也是当时石景山区唯一的一家照相馆。1.骆驼馆骆驼馆是一户赵姓人家开的,名气很大,几乎成了广宁村的代名词。再早,骆驼馆位于南厂大门对面的路边。具体位置在增产宿舍与东铁路菜站之间。解放前,骆驼馆规模不大。因时常会有驮煤的骆驼队在此歇脚吃饭,被人们亲切的称之为"骆驼馆"。一九五一年前后,骆驼馆搬迁至现址,后划归国有更名为广宁村饭馆。解放后,村里的私人饭馆基本上已关张停业。偌大的广宁村只有骆驼馆独家经营,早晨卖油饼、麻花、芝麻烧饼和豆浆。正餐炒饼、烩饼成为远近闻名的招牌饭。改革开放后,广宁村饭馆的经营权发生改变,名称也被更改过数次。我的同学闻学利、翟惠琴高中毕业就分配在骆驼馆工作。2.理发馆早年间,广宁村只有一个剃头棚子,紧挨着王义小铺。解放后石电在老缝纫部那排房子办了个理发部,王力(王再跃的大爷)、肖玉元(肖淑兰的父亲)、李文华是理发员,后来王克祥(王立顺父亲)也是理发员。王师傅聪明好学理发的同时还学会了推拿按摩,村里人有个伤筋动骨的小伤,都去找王师傅给揉揉,王师傅几十年如一日为大家服务,分文不取。到了我小时候,那个理发部就关张了,王师傅到行政科当了电工。石电随后又开了个理发馆,就在现广宁办事处的所在地的平房里,理发馆的理发员大多是阿姨,有张燕的母亲、姚增信的母亲、杨艳茹的母亲。当年理发八分,洗理吹一毛二,如要刮脸加三分钱,抹头油再加三分钱。因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抹头油的业务随被取消。大概是一九七二年,这个理发馆搬迁到与煤球场一墙之隔的北厂礼堂的东北角。营业面积增加了不少,小学同学孙丰民的母亲、智其敏叔叔的爱人就是理发员。那时理发要排大队,石景山服务局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位于街里老户刘家旁边的黄金地段,又开了一家广宁理发馆。理发馆面积不足二十平米,三张白色铸铁的理发椅一字排开。一进门有个翻牌(就是镜框大小一块木板),木板上挂两排小木条,木条上面写着号码,进门的客人将木条翻过来,记住号码。问一下前面大概有几个人,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去办事。等时间差不多时,您再来理发。一进门,两边各有一条长板凳,供客人们休息坐等。几位理发师傅,总会找话题与您聊天保您不烦。张师傅白净面善、白阿姨特别爱聊天,她儿子是刘亚新、还有同学李忠信的母亲也是理发员。理发馆的头儿姓霍,大家都叫他老霍。论手艺霍师傅理发最好,服务态度也好,说话和气总是面带微笑。霍师傅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常年为一位瘫痪病人上门理发,其事迹曾经在《北京日报》上报道过。霍师傅退休后自谋职业,在村里骑个自行车来回转悠给大伙儿磨理发推子,因为挣不了几个钱,也歇手不干了。3.菜站村子里一共有两个菜站,早些年建成的菜站在村西头老车家对面的平房里。后改建成二层楼,菜站改成了广宁副食管理处。为更好的服务于石电职工,区里还专门在广宁路北,增产宿舍与东铁路宿舍之间,建起了副食商店和菜站,并在菜站东侧设置一处地磅。计划经济时期,广宁村住户按属地划分,分别在位于街里和东铁路的副食店,凭副食本购买粉丝、麻酱、碱面、鸡蛋等生活必需品。同学安震刚的嫂子、学弟何福利的母亲,都是那个副食店的售货员。比我大一届的田国庆(现名田伟)的父亲,是东铁路菜站的定价员。您千万别小看了这个职务,定价员负责到广宁地区的蔬菜供应种植地——麻峪生产大队(那时候农村以种粮食为主,麻峪村负责广宁地区的蔬菜供应),定购来年的蔬菜用量。负责过磅后的蔬菜定价,以及所要供应的菜站。东铁路菜站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地磅则建于七十年代。没建地磅之前,只能用杆儿秤一称一称的称出每份货物的重量。若是一马车成百上千斤蔬菜,称重是一件既麻烦又费时费力的工作。一次称个百十来斤的货物,至少需要三个人来完成。大杆秤由秤杆、秤钩、秤砣组成,秤杆上标有准星及重量刻度。大杆秤的秤杆有四分水管粗细,长度有一米五甚至更长一些。称杆上用尼龙绳或是皮绳,拴着一个看似成人拳头大小的铁砣。铁砣里有灌好的铅,杆秤前边有个铁钩使之勾住货物。大杆秤上有个铁环,铁环上有个用麻绳拴好的绳套,扁担从绳套中间穿过。两个人一边一个用肩膀扛着扁担,份量重的时候,要两个人一边一个用手托起来称重。然后,另外一个人根据货物的轻重,用手去拨动铁砣上的尼龙绳(或皮绳)。有时货物过多过重,使货物离地太高而无法识别准星时,要踮起脚来用手捏住尼龙绳(或皮绳),待放下秤杆后,再根据尼龙绳(或皮绳)所示刻度读出货物的真实重量。就这样,一秤货物至少需要三分钟,一车货物至少半小时。自从使用地磅称重后,程序就变得简单起来。不论是马车或是汽车,只要往地磅上一赶一开,重量便随之称出。当年,田国庆的父亲负责铸造村、广宁村、首钢、麻峪和高井四个菜站的蔬菜定价及分配去向。哪怕蔬菜供应再紧张,菜站都会保证优先石电、广中和石景山火车站三家食堂的蔬菜供应。那时在菜站后面居住的几户人家,几位年长的大妈,成天在菜站给食堂择豆角,为了挣几个零花钱,择一筐豆角也就一毛来钱。4.煤球场广宁村的村东口,有块儿占地大约十五亩左右的三角地,老人们称之为台湾岛。再早就是一片荒地,有个担挑子的混沌摊儿。解放初期,有个钉马掌铺子和几个小饭铺。在我小时,那就是黑乎乎的一片地儿,有个大煤棚就是广宁村的煤球场,如今已改建成为休闲广场。早先的煤球场,不仅着承担广宁村上千户居民的燃煤供应,还担负着麻峪村和铸造村几百户居民的燃煤供应。那时家里烧火做饭,冬季取暖都靠煤球炉。少部分家庭用蜂窝煤炉,煤球场可以送货上门。送煤的师傅们都骑着三轮车,每辆三轮车上,可以装上下两排十个方竹筐。每个竹筐可装五十斤煤球,每五十斤煤收五分钱运费。那时候,除了生活富裕的人家,或是缺少劳力的少数家庭用送煤到家以外,为省钱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自己到煤球场去买煤。周日的煤球场人山人海,买煤的人们排起长龙,没有三个小时甭想买上煤。入冬前,买取暖煤得连夜排队。例年冬季,企业职工每人有十六块五毛钱的取暖补贴,俗称煤火费。有暖气的家庭没有补贴。在咱们中国,据说是周总理定的,淮河秦岭以南没有取暖补贴费用。煤球场以出售煤球为主,也有少量的蜂窝煤和劈柴(北京话劈发第三声、柴发轻声)。煤炭公司负责煤球场的煤炭供应,同时煤球场自己也压制煤球。从我记事起,煤球场就是半机械化压制煤球,蜂窝煤都靠煤球场自己生产。据说蜂窝煤是民国时期一位山东人发明的,因为干净利于运输很快被推广。蜂窝煤需要三种物质互相依赖缺一不可,那就是碳、柴、煤。起初生火(很多人叫隆火),是用纸张和木柴点燃的蜂窝煤炭(主要由木屑渣和少量煤粉压制而成)。另外就是小块蜂窝煤和大块蜂窝煤,大块煤要比小块煤高三分之一。生火时,从炉子底部依次摆放碳、小块煤,待小块煤燃烧后再放上大块煤。另外是根据燃烧时间的长短,选择大小蜂窝煤块。那时,每户按定量供应燃煤。煤球场特别亲民,如果一不小心把蜂窝煤摔坏了,可以凭碎块换好煤,当然要付二分钱工钱。煤球厂有十来个工人,只有三位男师傅。一位是个头不高,长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马师傅。另一位苏师傅是个哑巴,这哑巴苏师傅心地善良特别能干。还有一位是六九届广中毕业生宋立民,宋大哥腿脚不太方便,家住广宁村小学校的西边。女师傅中有二高子的媳妇和王有林师傅的爱人(后来王师傅的爱人调入电厂工作)。那年月一入冬,街里就经常能看见摇煤球的,师傅们大多来自河北沧州。摇煤球的工具很简单:一个半尺直径的花盆;一个一米左右直径扁圆的铁丝网筐子;一把方头铁锹;一把齐头大扁铲。一般是俩人一伙将和好的煤面,摊在地上铺成两公分厚的饼子,阴干半天左右。然后用大扁铲切成小正方块,分批放进铁网眼的筐子里。为防止粘连加入一些干煤粉,放在倒扣在地上的花盆上用力摇,待摇好晒干后便可用于生火做饭。劈柴记不清啥价钱了,只记得买一毛钱的,能生(隆)三、四次火。经煤球场沿水泥路往西就到了街里,村里买煤的人们,倘若赶上好天儿还可以,如遇大风天气,您的身上脸上多少都得带点儿煤面。要是赶上雨天儿,您就得脚踩黑煤汤了。5.修鞋修车铺北厂马路对面往东十来米的污水沟盖板上,支着两间木板房子,房子不大,每间也就三四平米,一间是修鞋铺,一间是修自行车铺。一九七零年前后,因建派出所,修车铺搬到东铁路副食店西边的平房里,后因不景气干脆关张。别小看修鞋、修车的这两位师傅,都是服务局里面的正式职工,每月挣三十多块钱的固定工资呢。两位师傅平时工作挺闲,您想啊,那时候有几家有自行车的?鞋也基本上自己做,绝大部分人都穿布鞋,哪有多少人修鞋啊?即便是来修鞋也就是后根钉个铁掌,五分钱解决了。要不就是鞋滑子(鞋扣)掉了,缝几针二分钱也就解决了。从小到上高中之前,我就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母亲为我做。做一双鞋工序也很复杂呢,先是打咯粑,就是在一块木板上铺一块整布。上面涮上用白面和棒子面熬的浆糊,码一层碎布头,再摸浆糊再粘碎布头,大概要粘三四层,然后再粘一块儿整布,晒干后,剪成鞋底。每只鞋底要五六块摞起来,每块要用白布条包好边,然后用麻绳纳鞋底。鞋帮一般用新布做成,鞋帮有里有面,可以做成方口鞋,也可以做成五眼(系鞋带)鞋。再把鞋帮缝在鞋底上,北京人叫上鞋。做鞋最累的环节就是纳鞋底,最痛苦的环节就是在大腿上搓麻绳,最技术的环节就是上鞋。我家六口人,除父亲以外都是穿母亲做成的鞋。母亲还为我的几位叔叔做鞋送给他们穿,有时我半夜醒来撒尿,还看见母亲在灯下做鞋呢。一年四季的鞋,包括夏天的凉鞋,真是辛苦母亲啦。记得以前人们脚下穿的都是用布做成的凉鞋,大概是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才开始普及塑料凉鞋。那塑料凉鞋真好,男士的一般都是黑色的,女士的有红蓝绿几种颜色,几毛钱一双。塑料凉鞋唯一特点就是不结实,容易裂口。但不管哪出毛病,拿根儿废钢锯条,在火炉子里烧红,在裂口处一烫一捏就粘上了。6.邮电所北厂灰楼往西,水果摊东边有一排平房。其中有一间七八平米的房子,就是广宁村邮电所,门前立着的绿色信桶特别醒目。记得和谁约个见面地点,或者是家里有客人来,我们都会说,看见信桶站着那儿,我们信桶见。那时候,电厂为方便职工家属邮寄包裹和邮寄挂号信,就联系两公里以外的石景山邮电局,能否在广宁村设立邮电所。邮电局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特别强,两家一拍即合。电厂提供房子,邮局每周日专门派人,办理包裹和挂号信业务。随着业务量的加大,邮电所每周营业六天,但依然维持每周日办理包裹业务。邮电所那位师傅姓张,人称懒张,大人小孩儿谁叫他都答应。懒张以前是名投递员,专门负责为广宁村送信件报纸。之前的投递员,是位特别慈祥的老同志,总是先下车后,乐呵呵的将信件递交到收信人手里。自从懒张接班,无论给谁家送信送报,屁股都不离座,而且一准再让你帮忙为其它人稍带几封信,逐渐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懒张。邮电局在外设邮电所不是新鲜事,只要你提供场所就OK。一九九七年,我们单位基建期间,工地得有上千号人,邮政业务量特别大,离我单位最近的垡头邮电局也有三公里远,而且没有公交车。单位领导就协商垡头邮电局在厂里办个邮电所,邮电局提出了如下条件:提供场所,提供中午饭,每年买一定数量的纪念邮票,订阅邮电报。厂里都答应了,邮电所就在南门外开起来了。7.澡堂子广宁村老澡堂子,是在今天办事处办公楼的那个位置,还是石电为了方便职工家属建的,澡堂子的热水是靠一个烧煤的小锅炉供,那时候我才三四岁,只记得好像是一个星期只开一两天,男女共用一个,只是时间错开。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分析应该是供热问题),澡堂子就关了。我们洗澡得去四公里以外的金顶街东口,那里是首钢居民区,里面有个挺大的澡堂子,洗一次早是一毛钱。这一熬,就好几年,村里的人大多就不洗澡了,有的一年两年都不洗澡。夏天分不清谁洗不洗澡,因为天气热,在水管子洗头洗身子完全可以做到,可是到天冷了,谁洗不洗澡就可以通过闻和看甄别。我们小学同班同学就特别明显,尤其是女生,头发馊味,还发黏,脸蛋儿洗的挺白,可那脖子黑的还有嘎巴,我们都叫那种脖子是车轴。一九七二年左右,石电总算是在煤球场西面盖了个澡堂子,一三五男,二四六女的洗,周日休息。澡堂子有十几个喷头,中间有个大泡池。更衣间有几条大长板凳,有几十双拖拉板(木板拖鞋)。发电厂职工免费,家属凭医务室挂号证买澡票,五分钱一张,其他人一毛钱一张。后来又增建了一个女澡堂子,村里人洗澡就方便多了。我班某同学耐不住寂寞,多次爬到女澡堂子房顶,趴在天窗玻璃窗上看女人洗澡,被工人民兵抓个正着,扭送到公安局,拘留所待了一个星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确害人,我记得我姨奶奶从河北衡水深县农村来我家,我妈说带她洗个澡,干净干净,她就是不肯,那年她五十八岁,这辈子没当人面脱光过衣服,没洗过澡。我家那时农村亲戚多,内蒙的、河北的,经常来那些不洗澡的人,不是带来虱子,就是满屋的臭味儿,但是我家从没有烦过,只是亲戚走了,我妈不停的拆洗被褥。看澡堂子的师傅就是从前看疗养所的田大爷,那时候田大爷也就五十七八岁,但显得特别老。田大爷是河北沧州黄骅人,说话口音很重,但音调特别好听。这澡堂子后来也拆了,在东大楼二排西面,盖了个二层楼,那位置就是以前李锡铭家住的平房。一楼男,二楼女,洗澡条件改善了不少,有点儿北京城里浴室的味道了,挺规范,澡票也从五分钱涨成一毛钱一张了,王守礼师傅的爱人是浴室管理员。那年月到澡堂子洗澡带条手巾(毛巾),带块胰子(肥皂),就行了。初中时放假,我去爷爷家小住,爷爷那时候在西单商场工作,福利不错,发洗澡票,我记得是两毛六一张,可以洗澡也可以理发,好像还可以看电影(可能不可以,记不清了)。他带我去了一次西单浴池,我才知道洗澡可以不带手巾和胰子,休息区还有个铺,洗完澡还可以睡一觉,一人一个更衣箱,真是开了眼了。一九八九年我在苏州热工所工作一年。隔三差五就和同事混进南门桥外的印染厂洗澡,那里的澡堂子和广宁村的一样,才知道北京不比江苏先进啊!那年还去了一次镇江,晚上去了市里最好的澡堂子,两毛钱一张票,还有扬州师傅搓澡按摩,才五分钱一次。到了一九八零年左右,北京出了一种叫"华姿"的洗发水和浴液,印象是十块钱一瓶,据说是和日本合资生产的,我才结束了用胰子洗澡洗头的历史。8.粮店广宁村粮店,准确的说,应该叫广宁村"粮站",他的上级是石景山粮食局。粮站得有三百多平米面积,大部分是库房,居民排队买粮的地方也就是有十平米左右。我中学同班同学中,有一半儿是农业户口(我们是非农业户口,户口本上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知道火警电话09,匪警电话01,也是在户口本里看见的),他们是靠生产队分口粮吃,从没见过粮站如何卖粮食,有同学还特意跑到粮站开眼(北京话,看新鲜事儿)。我小时候,粮站有三四个叔叔卖粮食。卖粮食可是个力气活,一排大木柜子,有大米、白面、棒子面(玉米面),用个大铁簸箕铲出来,一次得铲个三十多斤,然后过秤,再到到买粮人的口袋里。站长姓齐,特别随和的叔叔,大家都叫他老齐,老齐在广宁村粮站干到退休。那时白面有三种:八五粉(一斤麦子,出85%白面),也叫标准粉;九七粉,也叫黑面;七五粉,也叫精面(富强粉),一般是春节每户才供应二三斤,够全家吃顿饺子的量。大米品种要多些,米柜里最常见的是一毛五分七一斤的米,我们叫机米,其实就是南方的籼稻,有时候是一毛四分一的米,我想应该是海南岛生产的大米了。人们最欢迎的是一毛八分九的大米,粒大油润香甜,我现在回想应该就是盘锦或五常大米。这一毛八分九的大米有多惹人爱,讲个典故,您就知道了。大概是一九七四年,我中学新来个教师,姓齐,就是齐站长的儿子。那时候大部分老师都有外号,学生们就给这齐老师起外号叫"一毛八分九",哈,那时候的孩子太淘气了。再有就是春节才能偶尔来的大米,小站稻(天津产的),一毛九分七和两毛一分三一斤的大米。棒子面嘛,谁都不爱吃,大概八分多钱一斤。小米只供应产妇,凭医院的出生证,再到粮食局开证明,可以买个几斤。我夫人一九八七年生儿子时,还走过这个流程,几斤小米去粮食局办手续,一扇猪排骨去副食管理处办的手续。那时候,家家粮食不够吃,寅吃戊粮是常态。每月24号,粮站人头攒动,因为那天可以买次月的粮食了。9.储蓄所村里的储蓄所和粮站一路之隔,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情。再早,储蓄所在骆驼馆西面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房子里,没有防盗门,没有报警器,在普通不过了。营业员和顾客同走一个大门进出,只是有个特别高的柜台里面有两张桌子,一个保险柜,一个记账一个审核两个人。一进门有一张课桌大小的桌子,上面有存单,有一瓶钢笔水,有一只蘸水笔(一般钢笔有皮囊,可以存水,蘸水笔,蘸一下钢笔水,大概可以写三四个字),供顾客使用。那时候存款种类很少,就是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两种。存折很简单,每笔业务都是用手填写,但营业员必须盖名章。那时我家隔个一年半载的,去存个五块八块。门口外墙上挂着一块儿不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银行广宁村储蓄所,每周一铁定休息。储蓄所搬到粮站对面后,大大改善了营业环境,房子不仅大了,还有个后院,营业员从后面进入营业区,顾客和银行之间多了一面玻璃窗,好像里面安全多了。但门口的牌子没变,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广宁村储蓄所"。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的冬季,储蓄所一夜之间换了一面大牌匾"中国工商银行石景山支行广宁储蓄所",不难看出,银行体制改革了,"村"字没有了,储蓄所地位提高了不少。一九八八年,我自己的小家三口人,全部家当是一架海鸥相机、一辆28凤凰自行车、一台三洋牌双卡收录机、一台雪花牌立升电冰箱、几件简单的家具和在储蓄所三百块钱定期存款。10.奶站最早的奶站就在现办事处位置的路边,实际上就是个牛奶发放点,那时全村也就有几十户订奶户。牛奶装在玻璃瓶里,瓶口用纸盖着用猴皮筋封口,一瓶奶是半磅。七零年左右,才有了奶站,就在煤球场对面澡堂子和理发馆中间,那个门里是石电"五七连"洗衣房。七五年十月,办事处收回奶站经营权,刚开始归东山居委会,后又搬到街里老储蓄所那儿了。一瓶奶(半磅)一毛九左右,奶箱也从木头箱改塑料箱,一箱24瓶。再后来,牛奶改成塑料袋包装了。七五年到九三年,发奶的大妈叫吴秀英,就是郑兰(小名毛毛)的母亲,我习惯叫她郑大妈。郑大妈再早是骆驼馆职工,得病回家休养,因将区长给她开的病好后可以恢复工作的证明丢失,未能再回骆驼馆上班,好端端的铁饭碗砸了。郑大妈不愿意在家闲着,就干起了发奶员,虽然一个月只挣二十多块钱,但心里挺舒坦。郑大妈厨师出身,不仅做饭水平高,还有文化,她的毛笔字写的特别好,能当字帖用。11.副食店副食店不大,一进门左手卖猪肉和卖豆腐豆制品,迎面的柜台左边是糖果糕点烟酒茶叶,右面是副食调料油盐酱醋,进门右手是蔬菜和水果。一到夏天,副食店的水果就搬到外面的大棚子里面卖了,其实也没有几样水果,我记得是苹果、鸭梨、大枣、橘子、香蕉、应季的水果有桃、杏。到了盛夏,西瓜上市了,这大棚子就热闹起来了,一共三个售货员根本忙活不过来。一个男售货员人称老吴,我小学同班同学吴宝生的爸爸,两个女售货员,其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姓门,人称老门,后来成了我小学同班同学刘淑果的婆婆。那时候西瓜五六分钱一斤。赶上河南、河北整汽车的倾销的时候,西瓜三分钱一斤。西瓜摊旁边有两口大水缸,放着好多西瓜,缸里面用水龙头往里灌自来水降温,那时候也没有冰箱,就是自来水降温。西瓜摊上面有个木头框子,三面玻璃,一面笼布(白色网眼纱布),里面摆着切成牙的西瓜,五分钱一牙儿,打我记事,这西瓜就是五分钱一牙儿。西瓜堆旁边放个大竹筐子,供人吃西瓜吐籽和扔瓜皮。那时候吃的起西瓜的家也不算多,这筐里的西瓜籽就成了好东西。我经常看见有几个孩子,老在筐里捡瓜子,然后在水里洗洗,晒干后炒着吃,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酸酸的。大棚一般晚上七点收摊,夜里担心水果丢了,就雇了张群他爷爷打更,一个月给十块钱工钱。12.百货店街里的百货店是从石电合作社衍生出来的,合作社的售货员都是石电职工,第一任合作社主任叫杨玉喜。售货员冯叔叔是同学冯光明的父亲,虽然人脱离了石电,但至今还住着石电的房子。百货商店是我记忆最深的地方,哪个柜台卖什么,店里有几个售货员,我至今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家在解放宿舍时的邻居,一个大眼睛的阿姨是卖布的,她有个儿子叫虎子。小学同学,三班的张文忠的妈妈是卖鞋的,二班的王昭雁的妈妈是卖服装的,学弟邹维军的妈妈是会计。现在的百货商店虽然已经被私人承包,并分包给了不同的商户,但是整体结构并没有破坏,原来的样子还在。我小的时候,百货商店的原址是个低矮、破旧不堪的房子,里面黑乎乎的,进去特别压抑,大白天都得开灯。说是百货店,一半是百货,一半卖糖果糕点。店里面真没几种商品,可是却来过一次特别的商品,而且是空间绝后的,以后再也没有在店里见过。一九六五年的一天,我妈去百货店买东西,偶然看见百货店正在卖缝纫机,就十台,一百五十块钱一台,上海生产的"无敌"牌缝纫机。我妈眼睛都亮了,因为她太喜欢缝纫机了,这送到家门口的好事,况且北京城里也不容易买到。她三步并作两步行,跑到北厂大门传达室给我爸打电话请示,我爸只回答了一个字"买"。我妈又一路小跑去储蓄所取钱,那年代,口袋里能有两块钱就是土豪了。辛亏我妈那时年轻,动作迅速,缝纫机还真搬回了家。缝纫机买来了,我家这六口人的衣服就再没买过,都是我妈我爸做。大一点儿后,我也学会了用缝纫机扎鞋垫,后来也可以做个裤衩子了。那时候的邻居们都时兴互相帮助,周日我家缝纫机基本上没有闲着的时候,给张家做个褂子,给李家扎个裤子。一直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缝纫机的家庭渐渐多了起来。百货商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原址翻建的,比路面高三层台阶,宽大的整块玻璃窗,特别透亮,正面女儿墙上面"百货商店"几个大红子特别醒目,左边和右边分别写着毛主席的语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长大后我去的北京和外地大街小巷多了,才发现,广宁村百货商店的建筑是标准模式,哪儿都有。前年回河北衡水老家,在护驾迟前营村里见过,今年十月去山西大同,在天镇县城也见到了。一进百货商店,正中心有一圈柜台,正对门口的柜台卖雪花膏、蛤蜊油、电池、肥皂、香皂、牙膏、牙刷、牙粉。左面卖儿童玩具,右面卖针头线脑。背面的柜台卖学习文具、笔墨纸砚、乒乓球拍、珠算、蜡笔。外围一圈柜台从右到左依次卖鞋袜、手绢(手帕)、毛巾、服装、布匹、锅碗瓢盆、五金工具。五金柜台前面的空地上面卖水桶扁担、炉子烟筒、凉席竹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店里买东西的人,大都是几毛钱的买卖。那时候,人见人爱的尼龙袜子才一块多钱一双,当然了还要0.1工业券。如果哪个售货员收了一张十块钱大票(大团结),都要登记号码,然后签上自己的姓名,假如是假票,售货员要承担责任。文革期间,店里经常揪出贪污犯,估计也就是把个块八毛钱揣兜里了。像这种售货员一经发现,就要开批斗会,然后只能在店里搞卫生,情节严重的会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后来为了杜绝贪污之风蔓延,专门设了收款台,收款台用若干根铁丝与每个柜台连接,售货员将购货小票和钱用夹子夹好,通过铁丝滑到收款台,收款台收款后再将盖了章的小票和找零滑回柜台。后来又改成电动装置,收款台有好几个小马达(电动机),收款的铁丝不停的循环,这的确省了售货员不少的力气。这种办法实行了一段时间,又改成了顾客自己拿着小票到收款台交钱。我小学同学冯光明的爸爸,还有一位帅哥左腿是假肢,就是收款台的收银员。设立收款台的办法不知道是谁琢磨出来的,一直沿用至今。百货商店里还有两个摊位,一个是修理钟表的,一个是修理钢笔的。后来就给撤了,估计是活不多吧。13.磨剪子磨刀村子北的鬼子山,我们也叫它磨刀石山。山不太高,约有三十多米。山里面有个磨刀石场,现在已经荒废了。我小的时候经常去磨刀石场玩儿,几个工人师傅每天就是用钢钎大锤凿石头,然后把凿下来的石头锯成30×10×20厘米的长条,将一面用锉抛光,就是一块儿磨刀石的成品了。其它尺寸的也有,但是三十厘米长的最多。加工磨石也有很多废品,有些尺寸不规矩,有些缺个棱角什么的。这些废品就被扔到废料堆里,随你往家捡。那时候家里的磨刀石,都是从磨石场废料堆里捡回来的。我记得爸爸还给爷爷家捡回来过一块呢,有一次三叔用自行车专门驮回木樨地家两块呢。村里大部分家磨剪子磨刀都是自己动手,磨刀石自然也都是捡回来的。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来一个带着孩子扛着板凳的磨刀师傅。磨刀一毛,开刃一毛二,磨剪子一毛五,调口(剪子的咬合)一毛八。这磨刀师傅为广宁村人服务了几十年,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绰号---磨剪子小辫儿。听村里老人讲,这磨剪子小辫儿,打两三岁起就跟着他爹走街串巷磨剪子。那时候他留着一条辫子,每当他爹给人家磨好剪子和刀,就在他头发上剪一下割一下,已证明刀剪锋利。如今他也是传承了他爹的手艺,也领着个儿子来村里磨剪子磨刀了。这两年,磨剪子小辫的儿子突然出现在广宁村里,他已经是七十来岁的人了,嘴里叼个烟袋锅子,操着山东德州话不停地和村里的老相识打着招呼。大伙听说他来了都出来捧场,问这问那,家里的刀剪都翻出来给他磨。他留着胡须叼着长烟杆,谁给他拍照都配合,时不时还摆个滑稽动作。他的磨刀磨剪子手艺不比他爷爷爸爸差,还多了品牌意识,随身带着移动广告牌,上面赫然写着"磨刀小辫来了"。14.缝纫部西瓜摊后面有两排房子,头排房子朝街开门的有邮电所、还有郭来子家,郭父是门头沟供电局老工人,六级工每月八十多块钱,他家有八九口人生活挺紧巴。朝后排房子开门的有马明(马惠新的父亲)家、陈国芳(陈景山的父亲)、叶颐年(叶天荣的父亲)家,学弟储景岚、学妹张玫家。朝后排房子开门的有马明(马惠新的父亲)家、陈国芳(陈景山的父亲)、叶颐年(叶天荣的父亲)家。后排房子西边有两间平房,我小学同班同学王淑兰家就住那儿,小学五年级她转学去了四川渡口(今攀枝花市),她家门前有个水管子。后排房子第一家就是缝纫部,这排房子还有四间是广宁村中学教师宿舍,魏涛、王光晋、张梦驹、安红军等老师住在那儿。石电还有一户人家也住那排房子,男主人个头不高,负责给电厂礼堂演电影跑片子,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羡慕他骑辆摩托车在路上穿梭,后来他是开一辆东风三轮摩托车。缝纫部的门脸很高,得有一米左右,登好几级台阶才能进门。不大的房子迎面有个裁缝台子,台子里面站着裁缝张师傅,张师傅慈眉善目白白净净,个子不高总戴个帽子。右手边也有个裁缝台子,里面站着裁缝苏师傅,苏师傅横眉立目黑黑乎乎,大高个子留个背头。苏师傅人长得高大威猛,但新机善良,他有个哑巴儿子在煤球场工作。苏师傅台子的对面立着一面镜子,做好的新衣服穿上照照那镜子,心里美的自己都能笑出声来。缝纫部还有一个加工间,里面有七八台缝纫机和一个熨衣服的台子。那年代,自己买布拿到缝纫部连裁带做,也比买成衣便宜个一两块钱。裁一件衣服大概是八毛钱,做一件两块钱左右。15.废品回收收站副食店东侧路的对面高坡上厕所旁边有个小院子,那就是废品回收站。小小的回收站有个简易的铁栅栏维圈,院里却常常门庭若市。回收站面积不大,却是个里外小套间,约十几平米。里间屋有四、五平米,房间里布置的很简单,一张三屉桌横在中间,桌子一侧贴于墙,上面干干净净,只摆放着一个枣红色的有些磨损了的小算盘。坐在这个房间的是一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胖姐姐,看上去三十几岁,她是出纳员,负责支付那些卖废品的钱款。外间稍稍大一些,约有十平米左右,这间主要是存放收购来的各种废品杂物铺。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阿姨,她是业务员,在这间负责称重,并将废品分门别类的整理好。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中,凡是家里不要的破东西或是捡来的破烂都是可以拿到收购站换成几角几元的人民币。收来的破烂废品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什么废铁废铜废铝等金属品、旧书报纸、碎玻璃、塑料制品,应有尽有。看着这些破烂不堪堆放满屋的废品,被阿姨给整理的井井有条,就知道阿姨是个干净利索人。阿姨家好几个儿子,人口多生活比较困难。她总是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灰色衣服,坐在那个专属她的小马扎上,一脸不苟言笑,却童叟不欺,很有爱心。她的小儿子叫王殿江,个子不高,很霸气挺仗义,身边总是随着俩个小跟班的同学。物资回收中心在北辛安有个总废品回收站,以前,每周日来个三四辆三轮车,在老信桶前面的空地收废品。村里的废品回收站是在七零年以后建的,能在这里工作也是正式职工铁饭碗。增产住的刘永和哥哥因腿有残疾,毕业分配就在这个回收站当业务员。现如今,废品回收站早已被走街串巷上门收废品的游商所取代,那个院子也变成了纯净水站。图片/康健磨刀师傅图片/孙路辉插画/喻非卿编辑/mj工作室 磨剪子小辫儿照片:孙路辉 未完待续。点击看上一季《石景山怀抱中的广宁村》第二季 下集预告:《石景山怀抱中的广宁村》第四季五、企业六、童年回忆授权发表版权为作者所有 未经作者允许请勿摘编转载 《石景山杂谈》商务合作 《石景山杂谈》投稿邮箱:shijingshanzatan .白癜风早期有哪些症状辽宁白癜风医院 |